在我所有的朋友中,与他相处的时间最短,其淡如水,但却相交最长,相知最深。
那是26年前的事了!在故乡眉山,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,他转学到我们班。一个月中我们几乎没有交谈,我似乎看见他爱在书本上用钢笔涂鸦,他也似乎偶然翻看过我写在书本空白处的所谓的现代诗。在高考前夜,大家都抛开了书本,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短暂的谈话。他向我展示了一幅他绘制的“四川名人地图”,我们大概谈到了古往今来四川的英才们“不出川则已”,一出川便“名动天下”。
高考之后就是天各一方。临别时我们互赠礼物,我赠他一本美术画册,他赠我一本朱湘诗集《草莽集》。两个在完全不同环境长大的人,都自称是“在苏东坡脚下长大的”,都酷爱文学,见诗就抄,还尝试写小说。在大学时,他热衷于体育,我痴迷于电影。我劝他多看电影,他欣然接受了建议,同时对古典音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我为报考电影学院研究生刻苦攻读时,他已开始在《银幕内外》杂志上发表影评文章了;当我拜师学习声乐和作曲,每日疯狂练声和练琴时,他也为音乐而疯狂,几乎把除工作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音乐,把除基本生活以外的绝大部分开销也用于音乐;当我给学生写《寄小读者》系列文章时,他已在大学开设影视鉴赏课,还举办过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讲座。
我们交往的方式异于常人。他说他从不是一个对“面谈”感兴趣,并且在这方面显示出无穷才华的人。我们20多年来主要靠通信保持联系,动辄写两三千字的长信。有一次,我半夜从双桥子步行走到沙河堡,到他就读的川师大中文系找他,两人绕着操场转了无数圈,那是我们的第一次长谈。大学毕业后,有三年时间,我们同在眉山教书,相距只有几公里,仍然不常见面。有一段日子没去他那里,他寄来一张明信片,上面写着:“花径早已缘客扫,蓬门终日为君开”。及至真的见了面,语言又极简,如同一僧一道,一个庄严,一个肃穆。两人决定去岷江河边走走,出东门,穿过一片田野,面对本乡先贤东坡先生描写过的这条河流,几乎同时想起“我家江水初发源”等诗句,同时有音乐在心头泛起,语言于是又变成了多余的东西。回去之后,他文思滔滔,写下一首长诗寄给我——《致我们闯进的那片田野》:“在大自然怀里坐了下去/这是两个干净的身体……”我保存着他的全部信件和文章。进入21世纪之后,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代替了鸿雁传书,其实消减了不少盼信读信的美好感觉。
我们的交往更多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,不拘于别人在来往上的礼节。吃不必大鱼大肉,清粥小菜即可;喝也不必咖啡香茗,一杯白开水即可,我们能从无味之中品尝出有味。我们都过着简单的生活,八小时以外,读书听音乐,关门即深山独处。偶尔也在一起小酌,但与老友聊天,即便无酒也醉。我们之间绝少物质上的投桃报李,绝少生活琐事的相互帮忙,甚至没有参加过彼此的婚礼,纯粹是精神层面的交流。我曾帮他寻到了他钟爱的卢梭的《爱弥儿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,他为我寻到了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。他了解我的思乡之情,特意送我一本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眉山县资料集》;我们在淘碟市场上会留心彼此的需要,他替我淘到了珍贵的周璇版电影《红楼梦》等;我的大部分古典音乐碟都是蒙他所赠,包括我的女儿音乐启蒙听的迪斯尼《幻想曲》;我从奥地利旅游回来,则专门给他带了一碟约翰·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……
我们都生长于中国的“十年内乱”时期,都曾经历过信仰的坍塌和重建,都曾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忧患,都曾受到来自西方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,我们都没有“廊庙之志”,在最激进最迷茫的青年时代,都曾痛苦地寻求出路,都曾努力寻找精神上的导师或者父兄,最后他找到了贝多芬,我找到了曹雪芹。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都想走出四川,但都没能走出四川;我们都曾幻想找一个能和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的爱人,但我们都失败了。
他有一张自画像,神情气质很像崔健,我有诗赞曰:“昂扬的黑发显示不羁的思想,明净的额头展露人性的光辉”。刚巧崔健被他引为精神上的师友和兄长,崔健的歌曾经震撼了他,撕裂了他,最终又还原了他。他视崔健为生命的唤醒者,精神的鼓舞者,摇滚的北岛和通俗音乐界的贝多芬。然而,他是很难画像的,冰山的大部分是在海平面之下。他有两次“文化之旅”,一次去云贵高原,在贵州青岩的布依族山寨,他假称寻访一位名叫“王问之”(枉问之)的大学同学,住进了当地人家里,目的仅仅为了体验少数民族的淳朴民风;另一次去河南参谒三位唐朝诗人的故居。在河南宜阳三乡李贺的故乡,可能是李贺的经历和当地奇美的风光激发了他的文人雅癖,他以李贺的口气给自己写了封信;此外他还邂逅了当地一位热爱苏东坡的古稀老人,一见如故,被引为座上宾,后来保持通信数年。他是多棱的,丰富的。文人的稚子童心、浪漫情怀、天马行空、奇情异趣,在他身上都混合存在着。
他有一段时间只读西方的书籍,拒绝承认中国的孔孟与老庄对他的影响。但我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,却常常“碰”到他。比如读到“静水流深”、“真水无香”这样的词语,感觉像是说他;老子的五千言《道德经》中的很多词语,“见素抱朴”、“知白守黑”、“被褐怀玉”等等感觉都在说他;《论语》中的“朋而不党”,“和而不同”也适合他;“一箪食,一瓢饮,居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,不知为什么,每每读到此,我的脑子里浮现的,竟是他在家里守着他的几百盘CD独自听音乐的形象。儒家与释道,入世与出世,兼济与独善的选择,是汉民族的文化基因,渗透进血液里的东西,容不得不承认。在朋友聚会时,他总是选择一个不起眼的位置,面带浅笑,听着,看着别人的滔滔不绝。但最洞察人性的是他,最悲天悯人的也是他;他的外表温柔敦厚,内心是金刚怒目;他的话最少,却击中要害;他不与人争,“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
世界在飞速变化,我们以某种不变的方式相互面对。我身边的朋友大都难免“心为物役”,终日为房子、车子、票子而奔忙,地位爬得最高的突然栽了,赚钱最多的突然发现癌症初期。我们仍然几年才见一次面,平时通过电脑和手机交流的永远是三大主题:文学、电影和音乐。将繁冗俗事,寥寥数语,一笔带过。每年的贝多芬祭日3月24日,他都会用他的方式纪念:他曾在带学生实习的一个小县城通宵听贝多芬的音乐,并为他写下一篇文章《3月24日》,在文中他想象了贝多芬在天堂的情形;另一个祭日,又写下一篇《愿闻雷声》,他把贝多芬的音乐比作雷声,比作自然,比作真理,“人在身体发生病痛挺不住时,需要输血,而在精神意志挺不住时也需要‘输血’——首先就是贝多芬的‘血’!”他给学生举办的古典音乐欣赏的讲座,标题是《你可能忽视了世间最美》。他说这辈子最想看到的景象,就是贝多芬在他的第九交响乐里所描绘的……
在今年的第一期“中国达人秀”上,我们认识了用脚弹钢琴的残疾人刘伟,还有双人舞者失去左腿的翟孝伟和失去右臂的马丽,他们感动了每一个观众。物质的艰辛、身体的残疾和心灵的痛苦,可能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礼物,有人因此沉沦,而有人把它转化成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等最美好的东西。由此才有了刘伟、翟孝伟、马丽的精彩人生;也由此诞生了曹雪芹和贝多芬等;还由此,有多少人缘着文学和音乐彼此走入了对方的心灵。
在前年“五·一二”大地震那天下午,所有的手机都没了信号,正当我在焦急万分担心家人的时候,惊喜地收到来自他的第一条短信,六个字:“地震,你平安吗?”我的心被重重撞击了一下,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删除这条短信!
在他因“个人问题”情绪最低落时,曾两次写下遗嘱,其中都有一条:日记和书信交潘波处理。这是我们从未当面道破的默契。我们珍视自己写下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断章残句的价值,一颗渺小的心灵也能折射出大千世界,所谓“滴水藏海”。
我的所有文章都会寄给他请他提意见,但惟独这一篇例外。我认为最高的赞美和最浓的情感都是埋在心底的,并且往往以最淡的形式出现。我们俩都不善于在酒桌上应酬,因为轻易说出的话并不珍贵!
人生本来不完美,甚至有痛不欲生的缺憾。但我除了有骨肉相连的至亲,还有心灵相契的知己,此生,足矣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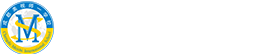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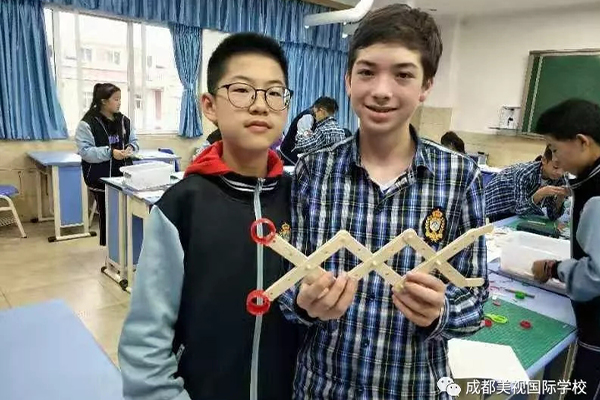


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